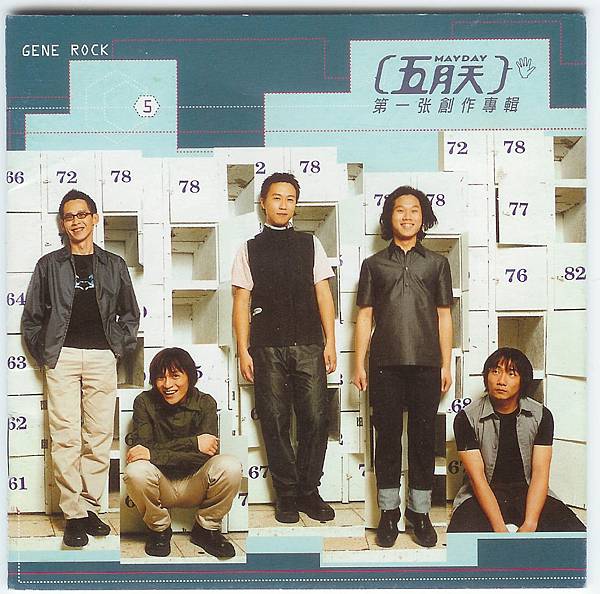龔文恬,Connie Kung,北一女數資班,台大電機系畢,南加大電機博士,前麥肯錫顧問,在大中華到紐約都有專案經驗。由公司出錢,住在紐約First Avenue,在一棟33層的公寓,每天可以眺望East River的晨曦。
現在是如新公司藍鑽石級主任,也即將在中國市場培養第一個年收百萬的部門。好久沒開的大腦風暴,身為主持人的福利就是能坐在學姊旁邊,近身感受暴風圈!
--
「走了一陣子,拿到了成果後,漸漸覺得自己每天在過的生活,比別人怎麼羨慕我的title重要。」
「知道自己在麥肯錫不會待久,在公司裡看到很多人最後只剩下錢,和生命的遺憾。簡言之,沒有role model。」
「上藍鑽、創四星之後,真的能感受到『被動性收入』的威力。——麥肯錫收入很高沒錯,但離職後就從此不再有收入。」
「ageLOC壟斷市場的技術競爭力。如果不講ageLOC,那就襯托不出Nuskin的特別。直銷只是一種行銷方式,但它主打的市場是什麼,才是重點。」
「在NS跟一般工作比,最大的成長與收穫?NS是一個鍛鍊心智的地方。有句話是『20-30歲靠專業賺錢,30-40歲靠人脈賺錢,40歲以後靠錢賺錢。』這躲不掉的。搞定人最難,但搞定人就搞定全世界;搞定人之前要先搞定自己。」
「其它工作都有主題,但NS的主題70-80%都在搞人,它的能量密度超高,你要密集面對情緒,才知道不夠愛自己。」
「所有老闆和成功創業家都是從業務做起,從年輕就開始學,比較會拿捏對人的分寸。」
「連麥肯錫最高的兩階都是做業務、扛業績,都要學會做人。從小是好學生的人都比較在意『做事』,對人的標準會很高、很狹隘。只要你放過自己,也會放過別人,那世界就會簡單和開心很多。」
「24-25歲的我,對成功有強烈渴望,但對成功的定義模糊。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掌聲,是別人認為你很重要和厲害。但你也不要戳破他。要給那些『追逐成功』的人時間。」
「如何培養對人的敏銳度?跌倒中學習。這是不二法門。」